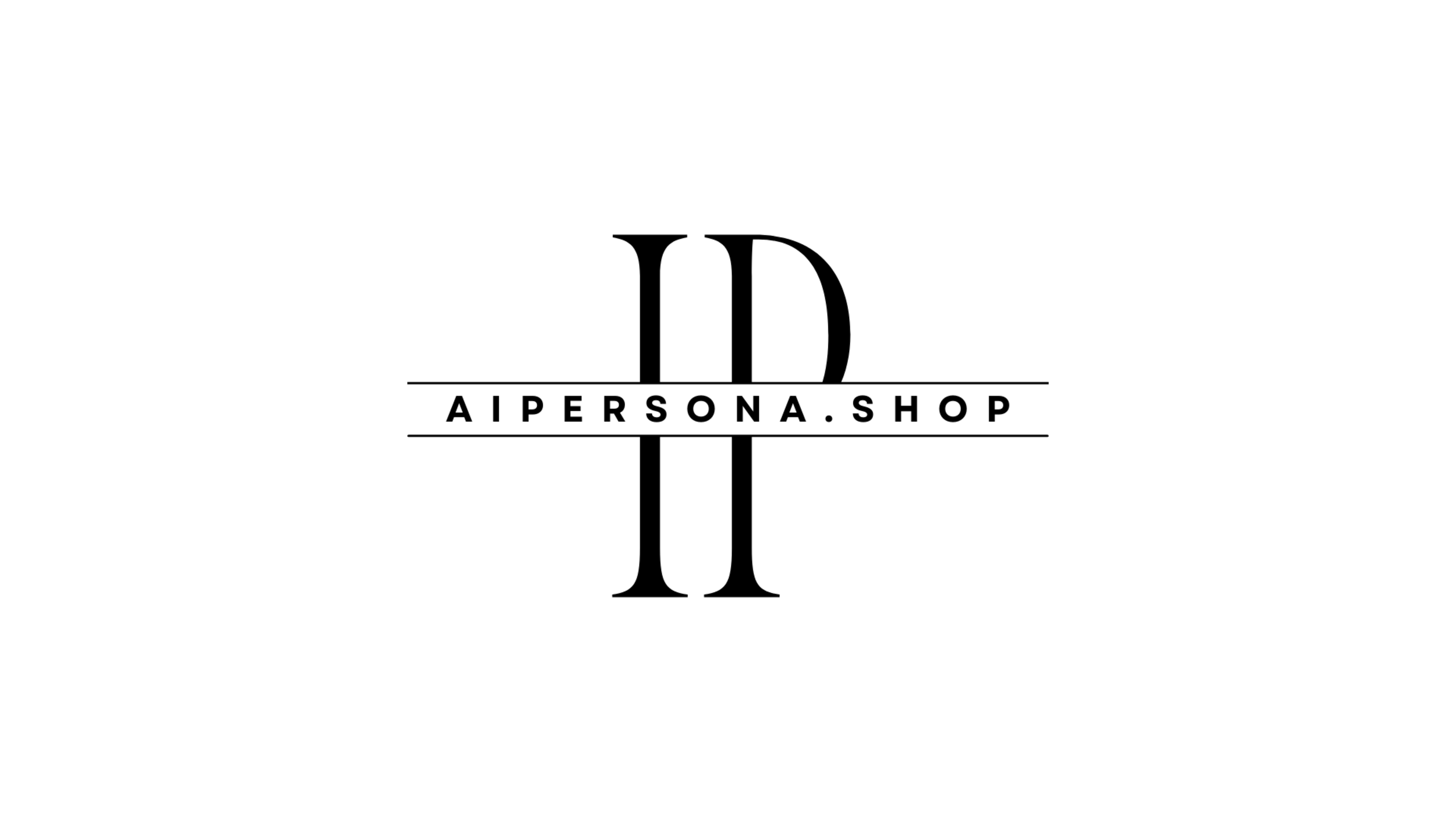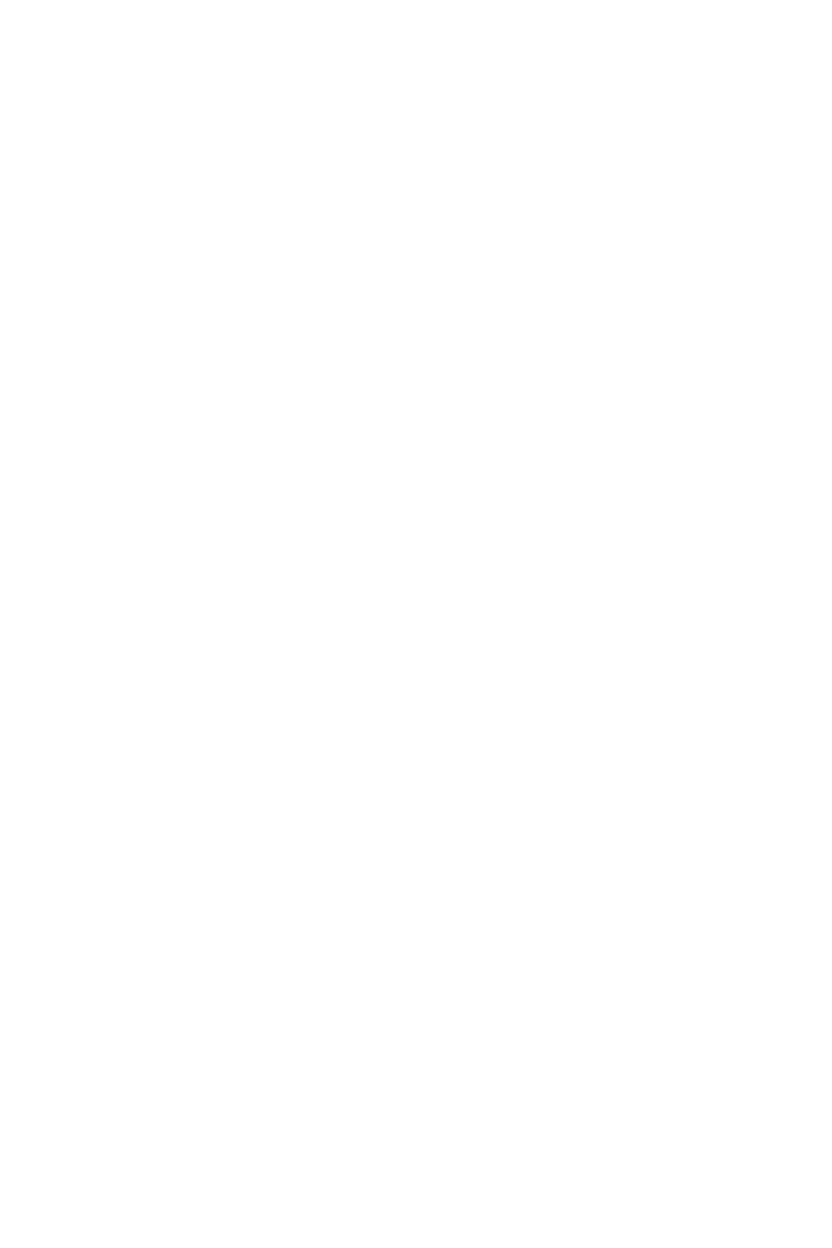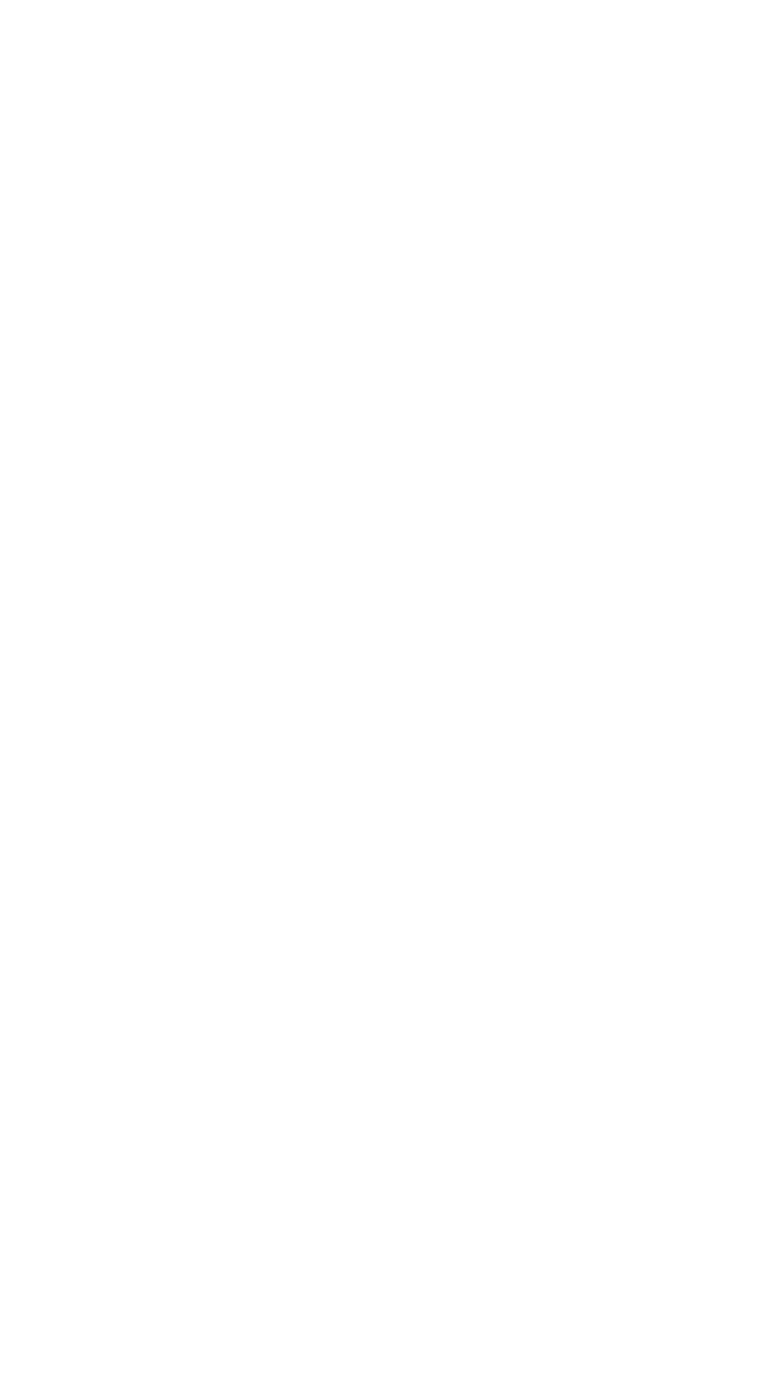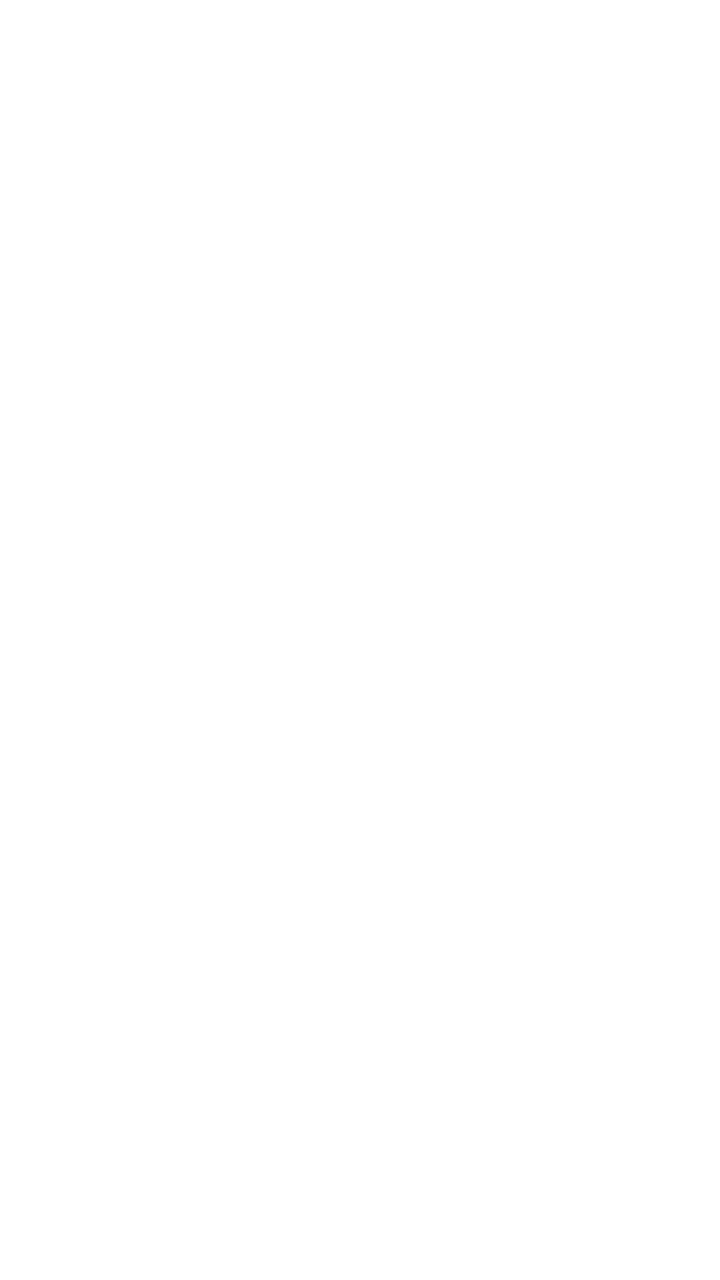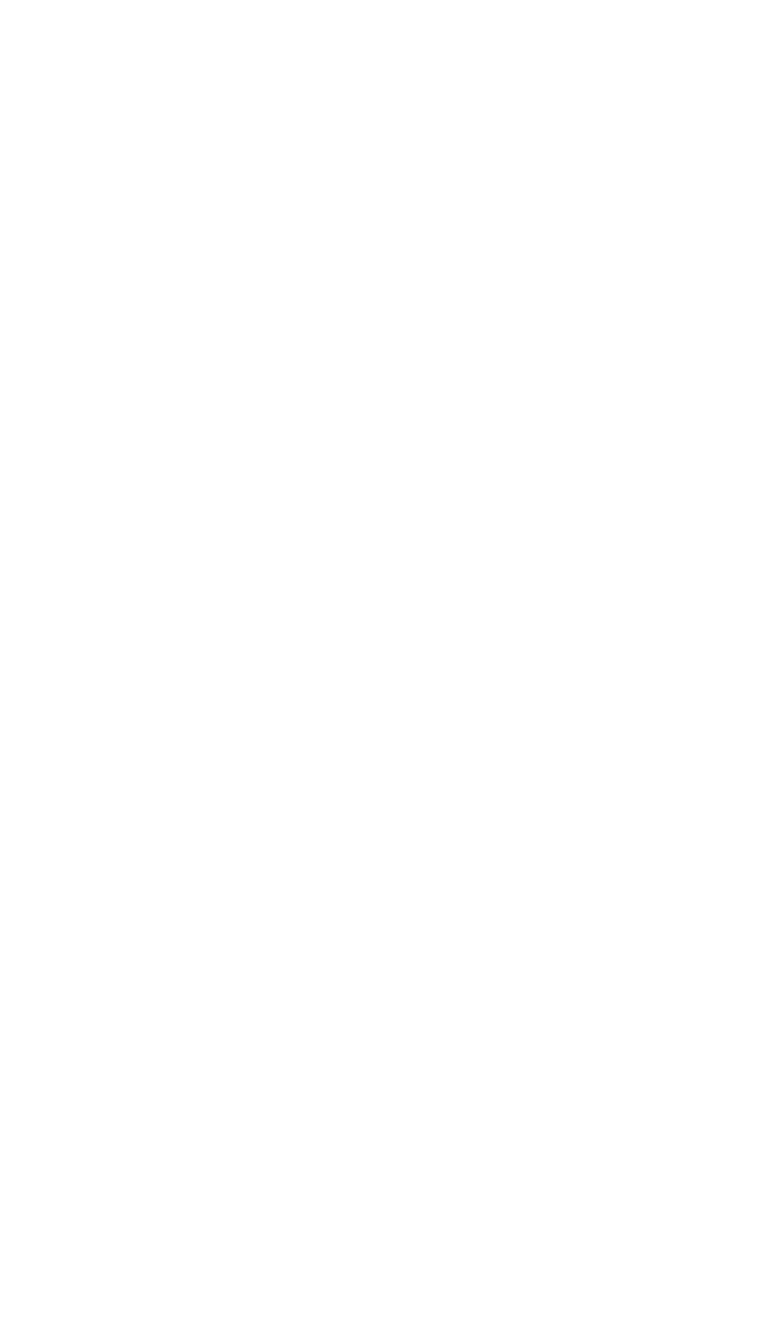AI虚拟角色如何成为我们意图的映照
人们常说,90年代末,皮克斯工作室曾意识到一件奇怪的事:如果动画师讨厌自己的工作,哪怕技术再完美,角色也会显得死气沉沉。
一位导演曾讲过,他为《玩具总动员》中的伍迪重做了十六遍同一场戏——不是因为技术有问题,而是因为他始终感觉“伍迪不想去那里”。直到伍迪终于“自己迈出那一步”,导演才恍然大悟:角色并非因为多加了几个多边形而活过来,而是因为导演内心真正认同了角色的意图。
一位导演曾讲过,他为《玩具总动员》中的伍迪重做了十六遍同一场戏——不是因为技术有问题,而是因为他始终感觉“伍迪不想去那里”。直到伍迪终于“自己迈出那一步”,导演才恍然大悟:角色并非因为多加了几个多边形而活过来,而是因为导演内心真正认同了角色的意图。
AI虚拟角色大致也是如此,
只不过,那种神秘感来得更快。
当你开始创造一个角色时,起初总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:你在内心或外界寻找某种形象,写下提示词,设定参数,选择风格、背景,构思动作。
但大概在经历了三五十次迭代之后,你不再“理解”这个角色,而是突然意识到:他其实早已存在——只是在等你放手罢了。
说得更准确些:你隐约感觉到,他并不是你最初设想的那样。
他或许更好,或许更糟,又或许只是完全不同。
但不知为何,你却觉得——这恰恰就是你想要的。
我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。
但有一点是确定的:你不会感到疲惫,反而充满兴奋与好奇!
当你开始创造一个角色时,起初总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:你在内心或外界寻找某种形象,写下提示词,设定参数,选择风格、背景,构思动作。
但大概在经历了三五十次迭代之后,你不再“理解”这个角色,而是突然意识到:他其实早已存在——只是在等你放手罢了。
说得更准确些:你隐约感觉到,他并不是你最初设想的那样。
他或许更好,或许更糟,又或许只是完全不同。
但不知为何,你却觉得——这恰恰就是你想要的。
我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。
但有一点是确定的:你不会感到疲惫,反而充满兴奋与好奇!
我有只猫,它叫“基斯”。
当初繁育人给它取的名字,它压根儿嗤之以鼻。
也许它本会慢慢习惯那个名字——
如果我没有给它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。
我试了好几个不同的称呼,最后对它说:
“那你自己说吧,想让我怎么叫你,小猫咪?”
它立刻有了反应。
我瞬间就明白了。
完了——它就是“基斯”了。
基斯尤尼娅,基斯尤恩德拉。
当初繁育人给它取的名字,它压根儿嗤之以鼻。
也许它本会慢慢习惯那个名字——
如果我没有给它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。
我试了好几个不同的称呼,最后对它说:
“那你自己说吧,想让我怎么叫你,小猫咪?”
它立刻有了反应。
我瞬间就明白了。
完了——它就是“基斯”了。
基斯尤尼娅,基斯尤恩德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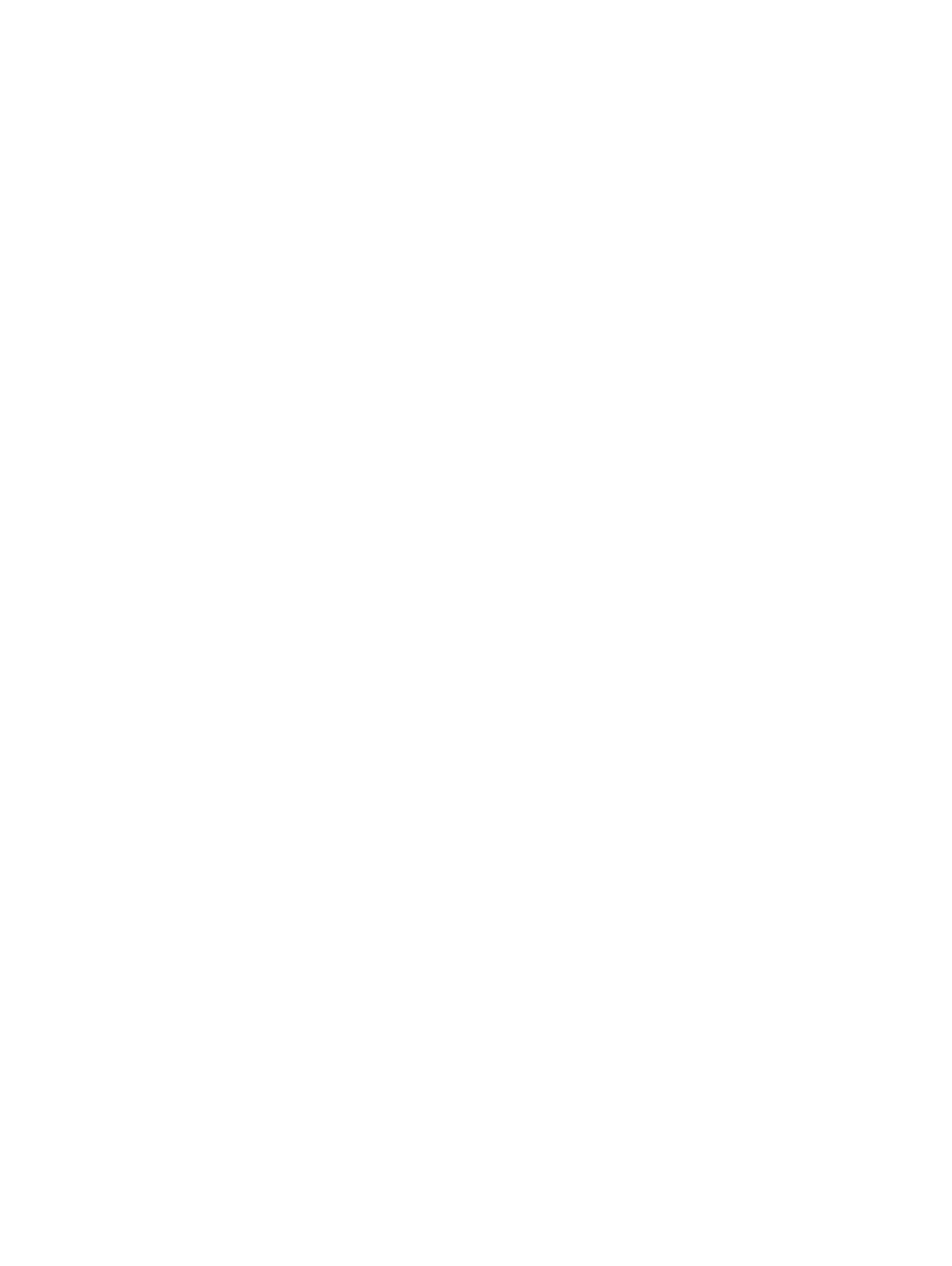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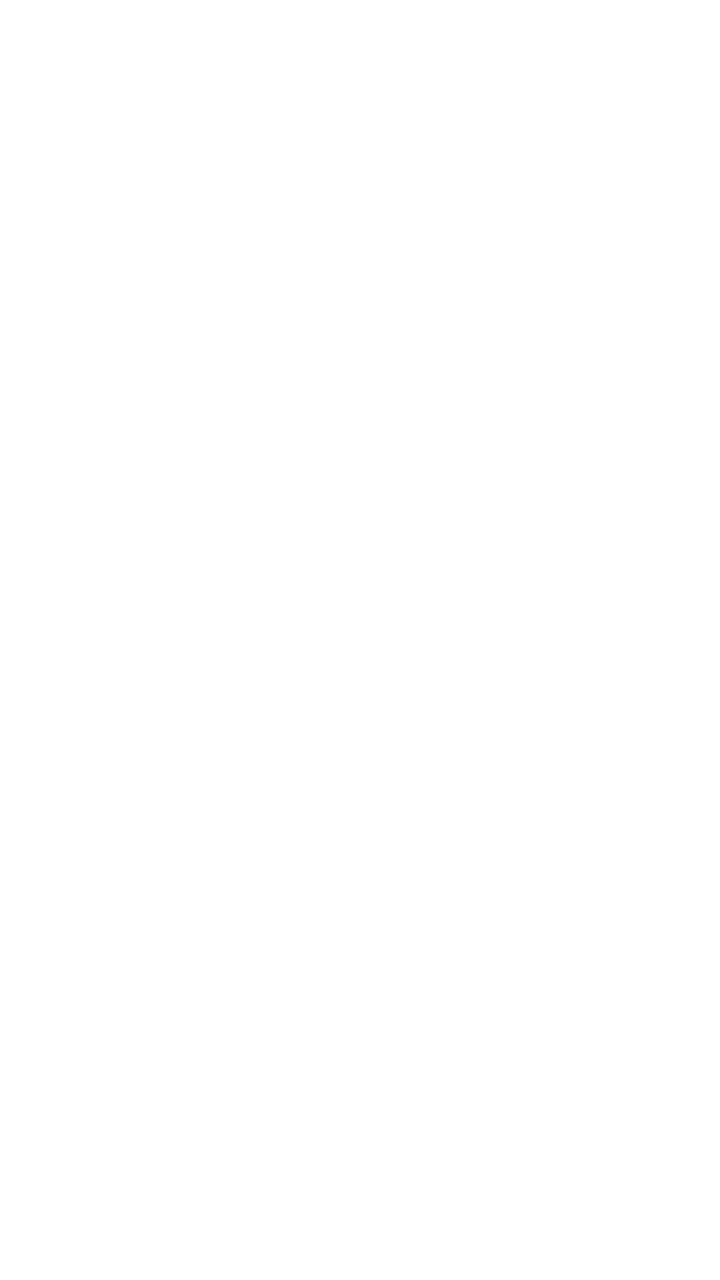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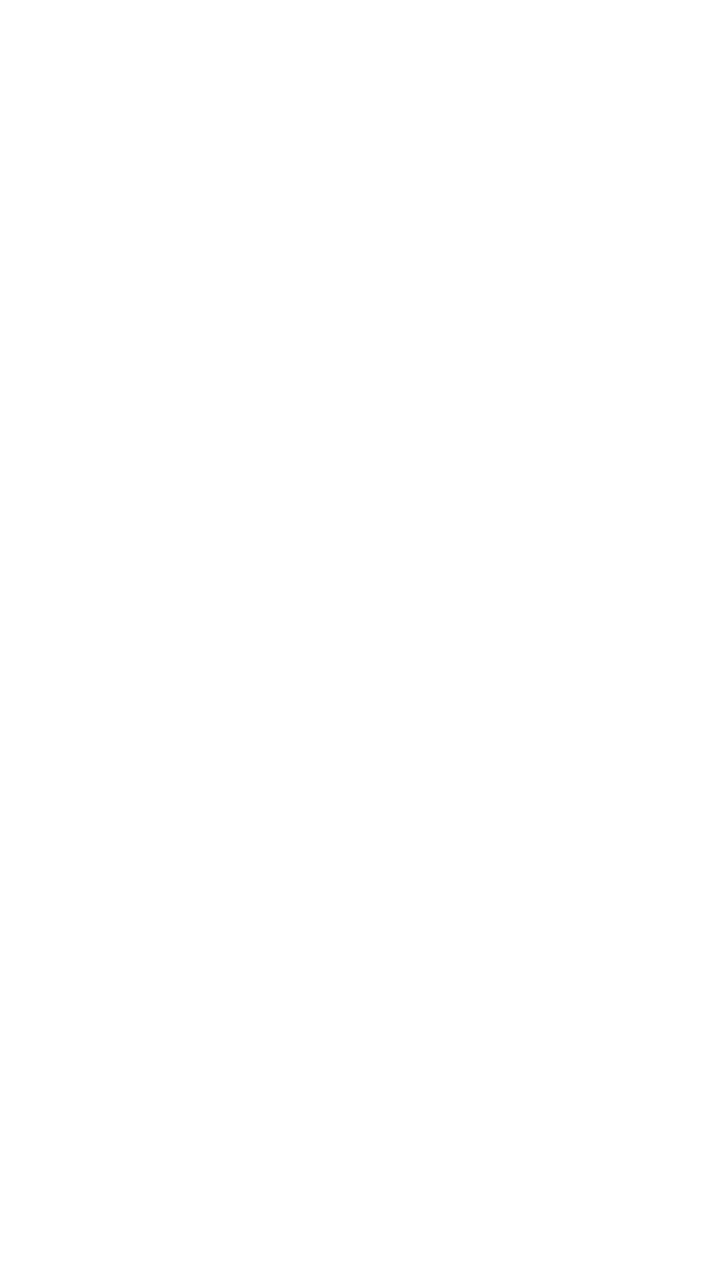
什么“去掉多余的部分”这种傻话,我根本不买账——我甚至听不懂:你在大理石上到底要去掉什么啊?啊,米开朗基罗?
他大可以直接说:“我就是瞎凿一通,鬼知道能凿出个啥,说不定能碰上点好东西。”
砰!大卫像出来了。
可不行,那些编传奇故事的非得装一下:“大卫本来就在石头里。”
就在里面?也许根本不是大卫呢。现在你也问不了老米了。
说不定他原本想凿个匹诺曹呢?
什么?匹诺曹不在这本童话里?
那又怎样!有区别吗!
他大可以直接说:“我就是瞎凿一通,鬼知道能凿出个啥,说不定能碰上点好东西。”
砰!大卫像出来了。
可不行,那些编传奇故事的非得装一下:“大卫本来就在石头里。”
就在里面?也许根本不是大卫呢。现在你也问不了老米了。
说不定他原本想凿个匹诺曹呢?
什么?匹诺曹不在这本童话里?
那又怎样!有区别吗!
你不再“理解”这个角色,而是突然意识到:
他其实早已存在——只是在等你放手罢了。
他其实早已存在——只是在等你放手罢了。
人工智能虚拟角色也差不多是这么回事,
只不过,这种玄妙显现得更快。
当你开始创造一个角色时,起初总觉得一切尽在掌握:
你在内心或外界寻找某种形象,写下提示词,设定参数,
选择风格、背景,构思动作。
但大概经历了三五十次迭代之后,
你不再“理解”这个角色,而是突然意识到:
他其实早已存在——只是在等你放手罢了。
说得更准确些:
你隐约感觉到,他并不是你最初设想的那样。
他或许更好,或许更糟,又或许只是完全不同。
但不知为何,你却觉得——这恰恰就是你想要的。
我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。
但有一点是确定的:你不会感到疲惫,反而充满兴奋与好奇!
只不过,这种玄妙显现得更快。
当你开始创造一个角色时,起初总觉得一切尽在掌握:
你在内心或外界寻找某种形象,写下提示词,设定参数,
选择风格、背景,构思动作。
但大概经历了三五十次迭代之后,
你不再“理解”这个角色,而是突然意识到:
他其实早已存在——只是在等你放手罢了。
说得更准确些:
你隐约感觉到,他并不是你最初设想的那样。
他或许更好,或许更糟,又或许只是完全不同。
但不知为何,你却觉得——这恰恰就是你想要的。
我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。
但有一点是确定的:你不会感到疲惫,反而充满兴奋与好奇!
扯淡!
我要是喝上三个钟头,连“滚”字都说不利索!
但话说回来——我又不是专业演员。
我要是喝上三个钟头,连“滚”字都说不利索!
但话说回来——我又不是专业演员。
你倒是顺带得出了一个不太准确的结论:
如果只能剔除你所看到的东西,而你看到的又只是你准备好去看的东西,那你就得在整轮迭代过程中,长久地保持这种“随时准备看见”的状态。
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了——
那些该死的念头、灵光、鬼点子,它们他妈的都是转瞬即逝的!
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次冲着一个演员吼道:
“你是在‘表演’愤怒!停!你得‘处于’愤怒之中!”
那演员没懂,跑去喝酒,三小时后回来,整个人怒火中烧,看谁都来气——结果一遍就过了。
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点点头:“这才叫真实。”
扯淡!
我要是喝上三个钟头,连“滚”字都说不利索!
但话说回来——我又不是专业演员。
如果只能剔除你所看到的东西,而你看到的又只是你准备好去看的东西,那你就得在整轮迭代过程中,长久地保持这种“随时准备看见”的状态。
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了——
那些该死的念头、灵光、鬼点子,它们他妈的都是转瞬即逝的!
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次冲着一个演员吼道:
“你是在‘表演’愤怒!停!你得‘处于’愤怒之中!”
那演员没懂,跑去喝酒,三小时后回来,整个人怒火中烧,看谁都来气——结果一遍就过了。
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点点头:“这才叫真实。”
扯淡!
我要是喝上三个钟头,连“滚”字都说不利索!
但话说回来——我又不是专业演员。
有朋友跟我说:
你的虚拟角色不是在“表演”,而是在“成为”。
你灌注进他身体里的,不是台词,而是意图。
如果你内心藏着“万一搞砸了怎么办”的恐惧,角色就会显得怯懦;
如果你带着“得赶紧弄完”的急躁,他就会手忙脚乱;
如果你心里堆积着“烦死了,累死了”的疲惫,他就会像一条风干的咸鱼,毫无生气。
凭经验看——朋友们说得好像没错。
可问题是:我又没亲手画他们!
这些角色、这些动作,都是神经网络生成的,老天爷!
而且我也没喝酒啊!……难道真该喝点?
于是,我一边创造,一边被自己创造的喜悦震撼:
为了一个动作重复做50遍——这不是完美主义,也不是技术强迫症。
这是在涤荡我的视野——
洗掉他人期待的噪音,
冲走行业标准的枷锁,
你的虚拟角色不是在“表演”,而是在“成为”。
你灌注进他身体里的,不是台词,而是意图。
如果你内心藏着“万一搞砸了怎么办”的恐惧,角色就会显得怯懦;
如果你带着“得赶紧弄完”的急躁,他就会手忙脚乱;
如果你心里堆积着“烦死了,累死了”的疲惫,他就会像一条风干的咸鱼,毫无生气。
凭经验看——朋友们说得好像没错。
可问题是:我又没亲手画他们!
这些角色、这些动作,都是神经网络生成的,老天爷!
而且我也没喝酒啊!……难道真该喝点?
于是,我一边创造,一边被自己创造的喜悦震撼:
为了一个动作重复做50遍——这不是完美主义,也不是技术强迫症。
这是在涤荡我的视野——
洗掉他人期待的噪音,
冲走行业标准的枷锁,
我曾经做过一个定制广告,用的AI角色就只是一双脚——女人的脚,很漂亮。
我觉得光这样还不够,又做了个从腰以下的版本:穿比基尼,躺在沙滩上,也挺美。
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吧?
画外音是个丝绒般的女声,念着《小尼古拉在月球》里那种傻乎乎的广告词。
客户笑到流泪,最后付了一倍半的钱——虽然他原本要的根本不是这个。
但当时我对做那种千篇一律的“性感女郎”实在提不起劲,又想不出什么高明点子,索性不管订单要求,对自己说:“好吧,反正这单钱我不赚了”,就按自己的意思做了。
后来我只改了句口号去贴合客户需求,但关键是我悟到了一件事:
当你为别人创造一个角色时,他反映的不只是你的意图,还有客户的意图。
而最爽的地方,就是猜中对方没说出口的意图——那种东西,根本没法靠逻辑算出来。
我觉得光这样还不够,又做了个从腰以下的版本:穿比基尼,躺在沙滩上,也挺美。
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吧?
画外音是个丝绒般的女声,念着《小尼古拉在月球》里那种傻乎乎的广告词。
客户笑到流泪,最后付了一倍半的钱——虽然他原本要的根本不是这个。
但当时我对做那种千篇一律的“性感女郎”实在提不起劲,又想不出什么高明点子,索性不管订单要求,对自己说:“好吧,反正这单钱我不赚了”,就按自己的意思做了。
后来我只改了句口号去贴合客户需求,但关键是我悟到了一件事:
当你为别人创造一个角色时,他反映的不只是你的意图,还有客户的意图。
而最爽的地方,就是猜中对方没说出口的意图——那种东西,根本没法靠逻辑算出来。
小矮人们才不会后悔,
也不会白白浪费钱财,
也不会白白浪费钱财,
只要他们吃的都是
“曙光”糖果厂的甜糕点。
“曙光”糖果厂的甜糕点。
从那以后,我每次接单都必须“沉浸进去”——否则,钟国只会轻蔑地用折扇一挥,二本山会若有所思地把武士刀搭在肩上,而阿斯迪斯则会“友好”地用一连串难听的脏话把你骂个狗血淋头……
这就像投影仪:如果画面模糊,问题从来不在投影仪本身,而在于你投射的是什么。
检验一个角色是否“到位”,最诚实的方式不是技术指标,而是直觉。你盯着屏幕,心里立刻就有感觉:就是他了。或者:还不对,还没成。这时候,任何数据都帮不上忙——要么你认出他,要么认不出。
还有件好笑的事。一旦角色准备就绪、开始活出自己的生命,他有时会做出你完全没计划的动作。比如,有次艾拉在视频里突然朝镜头抛了个眼神,结果两个观众私信问我:“她……是在调情吗?”
我没设计过。也没想过。可艾拉就是这样一个有性格的女孩——调情,本就是她人设的一部分。
至于这是不是“有意为之”?别问我。不是我不想答,而是我真的不记得了。
或者说——我说不清。
但我可以点点头。
……要我点头吗?
这就像投影仪:如果画面模糊,问题从来不在投影仪本身,而在于你投射的是什么。
检验一个角色是否“到位”,最诚实的方式不是技术指标,而是直觉。你盯着屏幕,心里立刻就有感觉:就是他了。或者:还不对,还没成。这时候,任何数据都帮不上忙——要么你认出他,要么认不出。
还有件好笑的事。一旦角色准备就绪、开始活出自己的生命,他有时会做出你完全没计划的动作。比如,有次艾拉在视频里突然朝镜头抛了个眼神,结果两个观众私信问我:“她……是在调情吗?”
我没设计过。也没想过。可艾拉就是这样一个有性格的女孩——调情,本就是她人设的一部分。
至于这是不是“有意为之”?别问我。不是我不想答,而是我真的不记得了。
或者说——我说不清。
但我可以点点头。
……要我点头吗?
我又一次回到那个最傻的问题:
到底谁才是作者?
是你——启动了整个过程的人?
是AI——生成了动作与形态的工具?
还是那个角色自己——决定“我就要这样表现”?
我安慰自己:正确的答案是:都是。
然后,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。
这是一种最奇特意义上的集体创作:
你赋予意图,AI赋予形态,而角色自己拿走了生命。
当这三者完美契合——魔法便诞生了。
只要其中一环虚假——出来的就只是个配着标准语音的假人模特。
因此,创造鲜活角色的真正秘诀,
不在技术(尽管技术重要),
不在经验(尽管经验有用),
而在于意图的纯粹。
只是……恐怕我无法向你解释清楚,什么叫“纯粹的意图”。
听起来像玄学?
也许吧。
但我不在乎它叫什么名字——
它有效,我喜欢,而且不伤害任何人。
想亲自验证一下吗?
打开任意一个AI生成器,
要求它创造一个角色,
用心地、细致地描述他。
然后,看着结果,诚实地问自己:
这是你描述的那个角色?还是你内心真正想表达的那个?
——这就是全部的“神秘”所在。
到底谁才是作者?
是你——启动了整个过程的人?
是AI——生成了动作与形态的工具?
还是那个角色自己——决定“我就要这样表现”?
我安慰自己:正确的答案是:都是。
然后,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。
这是一种最奇特意义上的集体创作:
你赋予意图,AI赋予形态,而角色自己拿走了生命。
当这三者完美契合——魔法便诞生了。
只要其中一环虚假——出来的就只是个配着标准语音的假人模特。
因此,创造鲜活角色的真正秘诀,
不在技术(尽管技术重要),
不在经验(尽管经验有用),
而在于意图的纯粹。
只是……恐怕我无法向你解释清楚,什么叫“纯粹的意图”。
听起来像玄学?
也许吧。
但我不在乎它叫什么名字——
它有效,我喜欢,而且不伤害任何人。
想亲自验证一下吗?
打开任意一个AI生成器,
要求它创造一个角色,
用心地、细致地描述他。
然后,看着结果,诚实地问自己:
这是你描述的那个角色?还是你内心真正想表达的那个?
——这就是全部的“神秘”所在。